李镇西:“培养公民,就是一个教育者最大的自豪!”——访丹麦斯莱特学校(中)

我们来到九年级A班的教室,老师正在讲民主辩论和民主运动,有两个讨论的话题,一个是关于人口贩卖,另一个是关于废除死刑。学生们分组讨论,发言者手里拿一个球,他说完了,便把球扔给另外一个同学,那个同学接着球便发表自己的观点。各个小组都在认真讨论,课堂气氛比较热烈。最后是老师统计各方观点的人数,让同学们举手表达意愿,比如:同意废除死刑的人有多少,赞成死刑的人有多少?学生们举起手中不同颜色的纸牌表达自己的意愿。


下课后,我通过翻译和老师交流,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堂英语课!他们的母语是丹麦语,所以英语课也是他们的“外语课”。我说:“我还以为是一堂社会课,或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政治课,原来是英语课。可我一点都看不出英语。既然是英语课,为什么不进行语言训练,而要讨论这些社会政治话题呢?”



他说:“我不对他们的观点做任何评价,话题只是一个工具,或者说一个载体,他怎么想我不管,无论人口贩卖还是废除死刑,在我这里没有标准答案,这是开放性的话题。我只看他们用英语表达这些观点是否正确。语言不能简单孤立地学,必须在生活情境中学,在自然而然的运用中学。”
我说:“通过这种方式,既训练他们的语言,又训练他们的思维,更扩大他们的视野。是吧?”

他说:“正是。我不是为考试去设计教学,要让学生在思考中,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,用英语表达观点,就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的一种技能。同时这种话题,对学生来说也是有用的。当然要训练语言,但更要培养思维习惯。这些讨论是开放性的,让他们形成思辨能力。”
我想到这是九年级的学生,便问:“这些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积累了,但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,恐怕仅仅用这种方式教学就不太合适吧?”
他说:“低年级和高年级的教学肯定是不一样的,低年级要让学生具备基本的语言技能,需要词汇积累,也要讲语法,但更重要的,是一定要让学生把语言作为一种应用,一定要让学生语言表达观点。”
说到对学生的考核,他说主要是根据每一个学生情况来考核,看他的语言能力是否有所提高。比如他会给学生一些资料,看学生的理解能力,他能否自由地运用英语自由地表达他的观点,包括语言的准确度……这些都可以看出学生的英语能力。
他一边说,一边拿出一个评分表给我看,上面有每一个学生的打分情况,而且都分类评分,比如有听力,有阅读,等等。他给我说,他不是统一打分,而是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来考核。这些考核,都是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分。
我还想问“操作性”,比如,怎么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来考核?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分,是不是太主观了?后来想算了,我又不是教英语的,越问越细,反而把有限的时间耽误了。
说到分数,他补充道:“这个分数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学生的一个参考,孩子不是被分数激励的,他们完全可以不在乎这个分数,而且大多数孩子都是不在乎分数的。如果有学生不想学习这门课,我不会用分数去‘激励’他,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分数,那我就和他的父母,还有他的其他一起来商量,用一种别的适合于他的方式去教他。并不同一个方式对所有孩子都是适用的。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式,但我会根据学生的情况不断去努力适应他们。”
不断适应学生,而不是让学生适应老师,这是最触动我的一点。
和英语老师交流完,两个中年男子走过来,面带微笑和我打招呼,握手。原来这是他们的一把手校长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。他俩把我带到一个会议室,并解释说:“本来应该在办公室正式接待您,但因为办公室正在装修,很抱歉只能在这里接待您了。”
我说:“没关系,这里很好的。”
校长说他看过我的有关资料,知道我也是一个教育者,出版了不少著作,愿意回答我关心的问题。
我问有多少时间可以交流。他说:“四十五分钟。”
我先问他学校的规模,他说,学校招收的是0-16岁的学生,共800个学生,除了这个小区,还有两个校区。
“有多少教师呢?”
“上课的教师有60个,还有40个辅助教师,也是教育者,只是不上课,他们负责学生的课外社团,各种俱乐部等等。在低年级,这些辅助教师还要在教室里帮助教师的教学。”

我问:“辅助教师帮助上课老师什么呢?”
他说:“如果一个孩子情绪不好,不想上课,来了心情也不好,辅助老师就会去帮助这个孩子,开导他。”
翻译郭老师特别给我解释,所谓“辅导教师”可以直接翻译成“教育者”,他就是教育者,只是不上课。
我问:“每个班都有两个老师吗?一个上课老师,一个辅助老师?”
他说:“我们的规定是每个班不能超过28个人,只要班额突破28个,就得分为两个班。另外,如过班额比较大,比如超过20个接近28个,就一定要安排两个老师。一个上课,一个辅助。”
我又问:“我们中国的学校有班主任,丹麦的学校有班主任吗?”
他回答说:“有的。为了保持对孩子教育的连续性,1-3年级、4-6年级、7-9年级都不换班主任,也就是说,一个班主任得陪学生三年。一般来说,班主任由教语言和教数学的老师担任。”
他还介绍说,为了不让一个班主任承担所有的负担,每个班都安排了两个班主任,分担学生的教育工作,当然以其中一个班主任为主,而且一跟到底,中途不换。
我想,这和中国差不多嘛!以前曾经听一些专家说,班主任是中国特色,最早是从苏联学来的,资本主义国家没有“班主任”一说。看来这个判断是片面的。几年前我在韩国,也请教过当地的老师,问韩国有没有班主任,答案也是肯定的。
我问:“请问您作为校长,平时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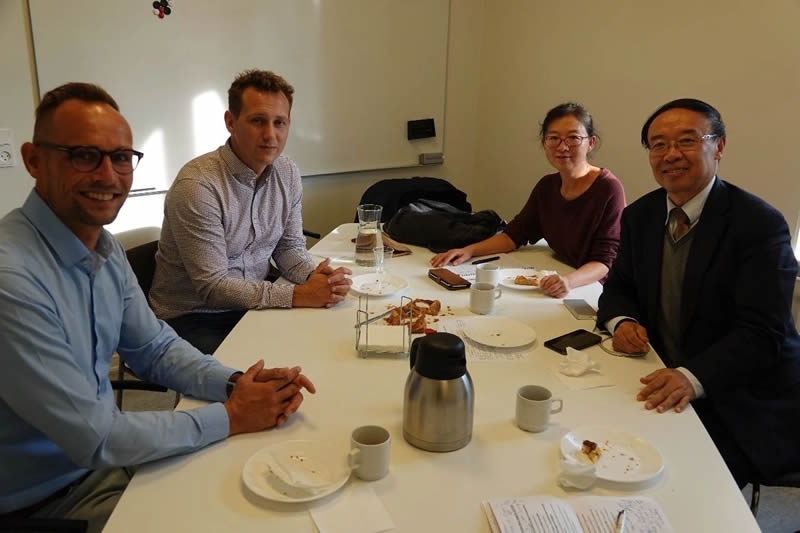
他说:“我的副校长面对学生,面对老师,面对家长,面对课堂,而我作为校长,面对的是当地政府,每年政府给我5500万丹麦克朗(相当于人民币5500万),如何让我的幼儿园和学校做得最好,到达到最好的效果,这是我平时考虑最多的问题。当然,学校其他方面虽然有我的副校长分管,但我们是一个管理团队,重大事情我们都要一起研究商量。比如昨天就发生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,我就得出面和家长打电话沟通。虽然昨天只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,但处理不好会影响整个学校,所以我们必须和整个管理团队沟通分享。”
我心想,和中国校长也差不多嘛!
我又问:“你对学校管理有多大的自由?比如学校发展的规划,比如课程设置,等等。”
他回答:“教育部有国家的要求,地方政府也有要求,但这些要求是一个宽泛的原则,只是一个要达到的目标和水平。我会根据这些这些目标制定我的学校发展计划,但是,具体开设什么课程,用什么教材,怎么教法,完全是老师自己的事。我不管老师用什么教材。我们可给他们许多教材,让他们自己选择。”
我问:“如果老师在这些教材范围里选不出他满意的,他可不可以自己开发教材,甚至自己决定开设一门课?”
校长回答:“当然可以。比如开学时,有老师说丹麦语这样上不好,这种教材也不好,我想以自己的方式用另外有更好的课程和教材,我当然会给老师这种自由。但我会经常去看这个老师的课堂。这个班级要达到的目标所采用的方法,不是我的任务,是老师的任务,老师怀着责任感去教就行了,只要他能够达到教育目标。”

我问:“你们如何管理教师呢?如果对教师不满意可以解聘吗?”
他回答:“我们是公办学校,但我是校长。老师在这里工作,都是我雇佣的,如果对老师不满意,我是可以解雇的。这是我的责任,我必须保证每一个老师都是合格的。”
我问:“丹麦有职称评定和评优选先之类的事吗?”
他回答:“没有。”
我问:“没有这些激励措施,那你如何保证你的老师的责任心和专业能力呢?”
他回答说:“打个比方吧,我会把有经验的老师和缺乏经验老师组合在一起,让有经验的老师去带一带没有经验的老师,帮助后者提升。当然,学校里哪个老师强,哪个老师弱,我心中是有数的。我经常给老师一对一的对话交流,我会利用这种交流的机会,把我的赞赏或我的建议传达给他,鼓励或帮助老师。在下一年制定学校计划的时候,我会把许多优秀老师的建议和想法写进去,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参与学校发展,他会觉得自己被欣赏。”
我问:“如果遇到确实不负责任或者经过努力也无法达到教学要求的老师,怎么办?”
他说:“这样的老师肯定有。我会给他机会,分管校长会找他谈,给他指出问题,提出改进的建议,我也会找他谈。不会一下就解雇。但如果实在不行,那我肯定不会再用了,我会亲自找他谈,说你不适合在这里工作了。但丹麦有强大的工会,会维护每一个老师的权益,比如工会规定,被解雇的老师根据一定工作年限,会多付六个月的工资,让他有半年的时间找到下一工作,所以不会把老师一下子推向极端的境地。我的压力不大。当然,有时候被解雇的老师不一定都是不称职的,也可能是因为预算不够,不得不减少老师。”
我问:“教师之间的工资有差别吗?”
他说:“在丹麦,校长无权决定老师的工资是多少,每个老师所教的年级和科目如果相同,那工资是一样的。12年中,老师的工资有三个晋升的阶梯,只要没有大的失误,只要到了那个时段,自然就晋升。只要没有大的问题,根据年限老师的工资自然增长,所以我没有压力。”
我问:“丹麦的工资在社会上比起来,是属于那种档次?”
他回答:“属于中等吧,比医生、警察高。我们老师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,感觉社会地位不错。当然,我们是民主国家,媒体上什么声音都有,也常常批评我们公立学校的老师。这很正常。但总体上讲,我们还是很受尊重的。我们这个职业很有安全感,整个保障体系也很完整。”
我问:“老师们的工资都一样,也没有额外的奖励,那他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动力从哪里来?”
他看了看我,然后非常郑重地说:“我们的老师,作为公立学校的教育者,的确特别自豪我们的工作,是把我们一代一代的孩子塑造成一个适合民主社会的人和公民。到他毕业的时候,他已经是丹麦的公民,这就是我和我们的老师,作为丹麦公民,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,这就是最大最大的激励!培养公民,就是一个教育者最大的自豪!”
培养公民,就是一个教育者最大的自豪!听到这里,我热血沸腾。
(未完,待续)




